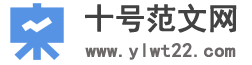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(三)
四、 学科整合与道通为一
各学门之方法学问,并非楚河汉界,不相交通,不妨相互参照,彼此激荡。李约瑟在大学时代所受训练,是生物化学的专业;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以医学与生物学著称,李约瑟当过圣约翰学院院长;后来转向研究中国科技史,竟能独立而杰出。何大一院士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、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物理,之后再去哈佛大学研读医学院。由于专业是物理非生物的训练,所以思考方法别开生面,研究方法蹊径独辟,有助于他日后的成功与卓越(童元方《为彼此的乡愁》,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)。
旧元素的新奇组合,能创造发明新产品,古今实例极多,如将葡萄酒榨制机和硬币冲压机作新奇组装,于是古登堡(Johannes Gutenberg,1398?—1468?)发明活字印刷机。数学和生物学结合,门德尔(Gregor Johann Mendel,1822—1884)创立现代遗传学之新学科。爱迪生异想天开,将并联电路连接高电阻灯丝,而发明了照明系统。诺贝尔奖得主欧瓦雷斯(Luis Alvarez)将天文学与古生物学作科技整合,于是发现行星陨石撞击地球,解答了6500万年前恐龙快速灭绝之科学谜团[史提夫·瑞夫金(Steve Riukin)、佛拉瑟·西戴尔(Fraser Seitel)著,甄立豪译《有意义的创造力》第6章《让灵感碰撞源源不绝》]。由此可见,新奇组合,造成惊人碰撞;扭转假设,容易发现不同世界;唯有跳脱旧有,才能开创新局。
闻一多(1899—1946)《伏羲考》指出,作为中华民族象征之“龙”的形象,是以蛇身为主体,接受了兽类的四脚,马的头、鬣和尾,鹿的脚,狗的爪,鱼的鳞和须,新奇组合而成。美国科学家L.托马斯(L.Thomas)《顿悟:生命与生活》中亦表示:凤凰、麒麟、龙、斯芬克斯(人面兽身)、格力风、圣陀尔、曼提考、根刹……各种不同之神话形象,“组成它们的各个部分,都是人们十分熟悉的”,但“从整体上看,却是新奇的”。换言之,“它们的奇特,在于它们是各种已知生物的奇特的混合和拼装”,由此得出一个结论:“有生命的事物倾向于聚合,相互之间建立联系,尽可能和睦共处,以求在各方的体内求生,这也许是大千世界的根本之道。”(滕守尧《对话理论》,台北扬智文化公司1995年版)将一些分离的要素、概念、事物、设想,经由新奇组合,促成互生、共荣的态势,应是注重对话之当代文化的主旋律。
文学作品的研究,与文学理论的研究,往往楚河汉界,甚少交通。殊不知“作品是理论批评的土壤,不研究理解作品,就难于研究和理解理论批评的实际”。因此,程千帆先生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特色,是将作品与理论作相济为用之整合,一则“以作品来印证理论”,再则“从作品中抽象理论”。尤其是后者,主张研究古代文论,要用“两条腿走路”:一是研究“古代的文学理论”,二是研究“古代文学的理论”。两者之中,尤其着重从文学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(以上参见程千帆《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》,《程千帆全集》)这种视野与方法,是企图“从古代理论家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以外,再开采新矿”,也许就能有新的发现,真能获得更多的借镜和参考价值。笔者研究唐宋诗学,曾经翻检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唐诗补遗》,探讨其中27首读诗诗,而后知唐人而开宋调者,晚唐风韵为宋人所宗法者,此中颇可考求而得(张高评《唐代读诗诗与阅读接受》,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《国文学报》第42期)。又翻阅《全宋诗》之读诗诗,得40家92题131首,宋人之学古通变、审美意识、诗学典范、自成一家,此中多有体现(张高评《北宋读诗诗与宋代诗学——从传播与接受之视角切入》,《汉学研究》第24卷第2期)。凡此,皆从唐诗宋诗“作品中抽象理论”,可据以补充唐宋诗学批评史之不足。
方法学之演练,必须自我要求,真积力久,自然运用裕如,胜任愉快。譬如系统思维,为创造性思维之一。系统分析,从客观对象的整体观念出发,研究整体与部分、整体和层次、整体和结构、整体和环境、整体和动态的辩证与统一关系(参考刘长林《中国系统思维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;姜义华、瞿林东、赵吉惠《史学导论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)。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、刘青峰教授,“中央研究院”许倬云院士,借镜其方法理论,分别探讨思想史与历史观念,都获得卓越之成果。金观涛、刘青峰《兴盛与危机》一书,强调中国封建社会,是个超稳定系统,这是它能长期延续的原因。将系统论、控制论整体研究方法以及数学模型的方法,借镜运用到历史研究中,以解释中国社会、文化两千年来的变迁与特点。转化现代科学方法,诠释解读中国历史,企图梳理出发展之规律,包遵信品题本书,称许为“史学领域的新探索”,尽管学界评价褒贬不一,何尝不是一种历史观察?
许倬云《我者与他者: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》一书,将三千年来中国皇朝的中外关系,归纳为六个系统的变动,彼此间相互影响、牵动、调节与适应。这一涵盖多重系统的复杂组织,呈现为时时刻刻的调节与移位(许倬云《我者与他者: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》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),以为三千年来的“中国”,是不断变化的系统,不断发展的秩序,这也是以系统论诠释历史发展。由此可见,方法学之讲求,有助于创意之诠释。傅伟勋著有《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——“哲学与宗教”四集》以及《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》二书,《创造的诠释学与思想方法论》一文,提出层面分析法:实谓、意谓、蕴谓、当谓、必谓(创谓)等五大辩证层次,以之诠释大乘佛学、老庄、禅学,以及儒家思想,启发无限,值得观玩(傅伟勋《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》,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)。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印《中国哲学与诠释学丛书》,出版《佛教诠释学》、《儒家诠释学》、《道家诠释学》、《意境美学与诠释学》四书。以赖贤宗《道家诠释学》而言(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),以“本体诠释学”之视角,重新厘清道家哲学“有无玄同”的基本架构,阐明重玄道观的功夫论意义,参照海德格尔之哲学,重新阐明牟宗三、唐君毅先生道家研究成果的意义。比较哲学,别具一家。
黄永武先生《中国诗学·考据篇》一书,归纳条理,揭示方法,心得分享,金针度人,几乎触处皆是。如《校勘诗歌常用的方法》,提供三十一个法则;《诗歌辨伪法·伪诗鉴别法》提出八法:考诸本集善本、考诸他书征引、考诸时代先后、考诸进化历程、考诸文字体裁、考诸事迹制度、考诸思想风格、考诸目录序跋,堪称面面俱到,此真治学研究之方。《中国诗学·设计篇》,全书分八大主题,每一主题多提纲挈领、萃取精华、梳理条例、金针度人。如《谈意象的浮现》,归纳分析前人作品,提出九大法式;《诗的时空设计》,提示十五种式样;《谈诗的密度》,提出六种手法;《谈诗的强度》,提出十种“可以”;《谈诗的音响》,提出八种方案;《用心于笔墨之外》,亦提出八种方法;《“反常合道”与诗趣》,则揭橥七种金针。若此之伦,其类实多,方法学之强调,成为系列论著之特征。有门可入,有法可循,成为通航诗学海洋之津筏,即器求道,其则不远。有益文学其他文类之全方位研究,不只诗歌之探讨而已(黄永武《中国诗学·考据篇》,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8年版,《中国诗学·设计篇》,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年版)。
诗歌笺释学,清代十分繁荣昌盛。诸家笺释,大多以“诗史”、“比兴”为诗本质的基本假定,而以“知人论世”、“以意逆志”作为方法学。颜昆阳对于古典诗歌之诠释,别有创见,撰有《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》,批判清初朱鹤龄以下,历经冯浩以至民国张尔田诸家,深入诠说,形成三百余年之诠释史,以考察其源出与流别,辨析其方法之效用。除了重新评量“知人论世”与“以意逆志”二种主体性解悟方法之功能与局限,并加以调适外,另外提出“作品语言成规”的客观性限定,强调典故词义、题材类型、客观比兴三大方面之笺释准则(颜昆阳《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——中国古典诠释学例说》,台北里仁书局2005年版)。有助于清代诗歌笺释学之了解,进而可窥中国古典诠释学之堂奥。反思传统方法,提示诗歌笺释法则,亦足堪借镜。
傅璇琮先生为享誉中外、著作等身之知名学者。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,运用过多种治学的方法,随物赋形,交相运用,为其学术思想的形成,学术成就的获得,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大抵说来,有四大方法:其一,考据实证研究法,继承乾嘉学派实学之传统,体现在傅先生所有著述之中。其二,文学的历史研究法,如所著《唐代科举与文学》;其三,二重证据法,如所著《唐代诗人丛考》、《唐诗论学丛稿》;其四,诗史互证法,所著《唐代诗人丛考》、《唐才子传校笺》、《李德裕年谱》、《唐代科举与文学》、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等著作,都是从诗文互证、诗史互证的方法,提升学术之理性、说服性,成功开展了文学的社会文化学研究(傅明善《傅璇琮学术评传》,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)。上述这些研究法,值得文史学研究者借镜参考,转化汲取,作为今后研究之利器。
王兆鹏教授为当代治词名家,著有《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》、《两宋词人年谱》、《唐宋词史论》、《词学史料学》等专著。近著《词学研究方法十讲》,乃积累三十年来治学方法之经验之谈,虽名为词学研究,然其中方法可旁通通用于古代文学研究。书中提示之研究方法,共有八大层面:如词集目录、词集版本、词集校勘、词集笺注、词作辑佚、词作辨伪、词人考辨、词作系年等等(王兆鹏《词学研究方法十讲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),现身说法,金针度人,颇值得研究诗、词、曲、文之学者借镜参考。依此书《后记》,原来规划,尚有词人个体研究、群体研究、范式批评、定量分析、传播接受研究等等,亦皆重要之研究法,虽因故未能纳入,王教授相关论著,实已或多或少透露呈现,读者不妨按图索骥,其道不远。
有关方法学之著作,王兆鹏教授还有《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》、《唐诗排行榜》二书。运用统计方法,进行定量分析,以辅助诗词研究,很有创发意义。前书有一章专谈“定量分析”:《宋词作品量的统计分析》显示,创作量是成为著名词人的基本条件,或必要条件,但不是充分条件(王兆鹏《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)。《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》显示,宋词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,唐宋词的确具有南方文学的特征。而且宋词的发展历程有两个高峰:一是元祐前后,一是乾、淳时期。《20世纪词学研究格局的定量分析》,分别从词学研究之基本格局、研究队伍的力量分布,凸显出问题与对策。《唐诗排行榜》,分别就普通读者、批评型专家、创作型作家三种类型的接受众,在传播接受之历程中,对唐诗作品关注度之高低,影响力之大小,进行统计分析,而完成了唐诗名篇的排行榜。排行结果,崔颢《黄鹤楼》、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赢得第一、二名;王之涣《凉州词》、《登鹳雀楼》,杜甫《登岳阳楼》,分居第三、四、五名。李白、杜甫,向来齐名并称,排行榜之统计却显示:杜甫的名篇数几乎是李白的两倍,可见杜甫诗歌之公众关注度高出李白许多。排行榜同时印证:唐代的好诗名诗,六成在盛唐;唐代之七律、五律、七绝、五绝之第一,大抵名副其实(王兆鹏等《唐诗排行榜》,中华书局2011年版)。
读书治学,为求事半功倍,往往运用方法,借镜范式。犹行军用兵,多讲究兵法,参酌谋略。“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”而已,不可胶柱鼓瑟,不知合变。钱锺书综考历代名将之习用兵法与否,进而论述造艺、治学之四种性行,其言曰:
赵括学古法而墨守前规,霍去病不屑学古法而心兵意匠,来护儿我用我法而后征验于古法,岳飞既学古法而出奇通变,不为所囿。造艺、治学皆有此四种性行,不特兵家者流为然也。(钱锺书《管锥编》,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0年版)
“学古法而墨守前规”,是死法;“不屑学古法而心兵意匠”,是无法。死法,拘牵黏缚,不能奋飞;无法,天马行空,自由无度。“我用我法,而后征验于古法”,则自出己意复得古法征验可否;“既学古法而出奇通变”,是学古通变,创新出奇。前者,为“有法”;后者,已优入活法。以治学方法言之,则来护儿与岳飞之性行,值得借镜参考;岳飞之“学古通变”境界,更值得追求而力行之。
日本学者竹内好谈研究方法,分为鲁迅型与鸥外型:鲁迅引进西方,选择本国最需要的东西;而森鸥外则介绍最先进、最流行的理论。何者较好?大概见仁见智。王水照教授谈研究方法,可有两条途径:其一,从理论上去讨论;其二,从一些研究名著中找方法。以为后者较为切实具体。譬如,从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等近代文史大家去寻绎,梳理出研究的进程与方法。同时以为:“方法本身应是多元的,宏观微观都是必需的,旧学新知应该结合,各种方法应该互补。”(王水照《“鲁迅型”与“鸥外型”——研究方法谈片》,《鳞爪文辑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)笔者论述选题学之种种,大抵也是相容并蓄,以求相得益彰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陶文鹏先生,担任《文学遗产》副主编、主编,有机会审阅中国大陆学者投稿论文,对于学界之思维方式、研究模式、论文格局,较能全面而深入之掌握。陶主编曾分析《文学遗产》1980年复刊以来,27年之中,所刊载有关宋代文学研究之论文143篇,盛称“观念的更新自然引发研究方法的拓展”,宋代文学研究者不再故步自封,不再满足过去的研究套路,而是广泛运用新方法,故获得许多优秀杰出之研究成果:
(宋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)广泛地运用诸如文本分析、心理分析、定量分析、系统化、信息论、控制论、审美发生学、结构主义、范式论、中西比较研究等多种多样的新方法,或把传统方法同引进的新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,从而初步形成了多线索、多角度、多方位、多层次、多学科和谐并存各呈风采的研究局面,产生了许多立论新颖、见解独到而又逻辑严密、论证有力的优秀研究成果。(陶文鹏《开创宋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》,《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)
新方法之多种多样,传统方法与新进方法之有机结合,于是宋代文学研究之层面,生发“多线索、多角度、多方位、多层次、多学科和谐并存、各呈风采”,于是蔚为许多“立论新颖、见解独到,而又逻辑严密,论证有力”的优质学术论著。语云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”方法为文具之学,讲究方法,自然有助研究成果之独到新创。
研究必须讲究方法,解决问题往往仰赖工具,提倡方法学,是利人利己之行事策略。此乃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所谓:“取诸人以为善,是与人为善者也。”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建构《汉达数据库》,对于古代文献之全文检索,贡献良多。学界知而利用者,多能增强佐证,有助学术疑难之解决。如何志华教授善用《汉达数据库》工具,罗列对照《尚书》今古文、《史记》诸本纪、世家,而撰著《〈尚书〉伪孔〈传〉因袭史迁证》;潘铭基博士亦善用资料检索,考察《史记》避讳问题:胪列先秦两汉诸子史籍,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《新序》、《列女传》,以及《尚书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、《汉书》,与《史记》作对比研究,而撰成《〈史记〉与先秦两汉互见典籍避讳研究》一文。若于五十年前考察上述课题,因无计算机科技佐助,全凭人工记忆,完成研究将无可能。对于工具之驾驭与妙用,《庄子》曾揭示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一语,堪作治学之座右铭:妙用工具,而不要被工具所奴役!面对丰富而便利之知识信息,这是基本之认知。
方法,是一种工具之学,不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,而且贵能因事制宜,进行适切的转换性创造。美学思想家李泽厚曾批评康有为《大同书》中的“西体中用”,以为严重缺陷就在他缺少了“转换性创造”这一重要观念。康有为没认识“中用”不是策略,不是用完就扔的手段,而应成为某种对世界具有重大贡献的新事物的创造(李泽厚《漫说康有为》,香港《明报月刊》2006年5月号)。同理,上述所列各种研究方法,采用何者?必先相体裁衣,同时进行创造性转换,才不至于水土不服。创造性原理所谓“移植”、“换元”(田运主编《思维辞典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),可化用于研究方法的实际操作上。诚如李泽厚所言,方法不只是策略和手段而已,既不可“用完就扔”,亦不可穿凿附会。唯有转换性创造,或创造性转换,才能跳脱“预设法式”,由“死法”转化为“活法”(吕本中《夏均父集序》“所谓活法者,规矩具备,而能出于规矩之外;变化不测,而亦不背于规矩也”)。苏轼所谓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,差堪比拟。
(作者单位: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)
版权声明:
1.十号范文网的资料来自互联网以及用户的投稿,用于非商业性学习目的免费阅览。
2.《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(三)》一文的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,仅供学习参考,转载或引用时请保留版权信息。
3.如果本网所转载内容不慎侵犯了您的权益,请联系我们,我们将会及时删除。
本栏目阅读排行
栏目最新
- 1在农民收入调查工作动员培训会上讲话
- 22024年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自评材料(完整)
- 3公司党委党建工作总结报告【完整版】
- 42024年主题教育党建调研开展情况总结
- 52024年度区妇联关于党建工作述职报告(完整)
- 6关于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调研与思考(完整文档)
- 72024县党员干部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报告
- 8第二批主题教育研讨发言:时刻“以民为本”,听“实言实语”,办实事好事
- 92024关于党员干部法治信仰情况调研报告(2024年)
- 10局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落实自查报告(全文)
- 11XX国企分管领导关于党建设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研讨发言(范文推荐)
- 122024年第二批主题教育专题读书班研讨发言提纲(6)【完整版】